

從在街頭運動為原住民族權利奔走吶喊,到現在回歸「人」的自我詰問,達卡鬧的音樂之路走得激揚又灑脫。他不羈地說:「我創作、我歌唱,不是為了商業利益或聽眾的支持,對我而言,音樂就是生活。」
達卡鬧是從社運出身的歌手,他經常背著一把吉他,穿梭在各個原運場合,唱出原住民的弱勢處境。他關懷土地文化,以具詩意的歌詞,吟唱漂流木的生命歷程、八八風災對土地的傷害,就像是一位閱歷人間的吟遊詩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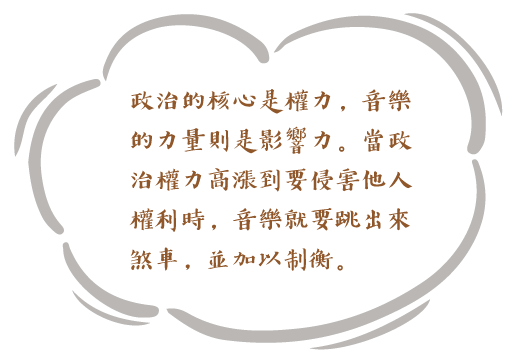
出生於屏東瑪家部落的達卡鬧,聽著部落老人家的吟唱歌聲長大,特別是將他帶大的祖母,每天一邊唱古調歌謠、一邊工作,無形中教導達卡鬧族群的規範知識與精神價值,啟發他對音樂的想像。「原來除了言語,人還有另一種聲音傳遞著文化,讓我們得以理解現在遇到的問題,以及未來要往何處去。」達卡鬧說道。

唱自己的歌,
原住民要做自己的主人
1970年代,校園民歌風靡全臺,李雙澤、楊弦、胡德夫掀起民歌運動,鼓勵青年學子抱起吉他,唱自己的歌。當時正就讀高中的達卡鬧,在這段時期接觸到吉他,他分享,「吉他便宜、好攜帶,是經濟條件不寬裕的族人方便取得的樂器之一,也因此成為影響當代原住民音樂相當重要的元素。」
民歌運動在都市地區盛行,但對部落地區帶來的影響有限。對族人而言,吉他僅是一種彈奏音樂的工具,而民歌運動真正的精神涵義──以創作、歌唱表達個人主體性與自由人權的觀念,並未真正於部落普及。包括達卡鬧,也是到臺北讀大學才逐漸了解民歌運動的精神,他語重心長地說:「那時候發覺,原來唱歌這件事,具有如此強大的社會意義。」

達卡鬧就讀大學時期,正逢原住民運動崛起,在原住民同儕及前輩的陶染下,達卡鬧開始省思自己的身分認同,「國家稱我們『山地同胞』,這非常汙辱人,且不是我們想要的名字,我們應該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名字、做自己的主人。」
民歌提倡的自由、主體性精神,與原運主張的理念匯合,達卡鬧和伙伴們走上街頭要求正名,並在1986年創作第一首歌曲〈好想回家〉,唱出主流社會體制下,原住民遭受的磨難與無奈。自此,音樂成為他向社會發聲、衝撞體制的武器。

《Am到天亮》具有強烈的原住民主體意識。
原音社不是音樂社團,
是社運團體
1990年代,原運進入休整期,運動參與者分裂成兩派:返回部落深耕,或是走入政治體制。當時的達卡鬧辭去教職,重返校園就讀花蓮玉山神學院,與同為神學院學生的許進德、依布恩成立「原音社」。達卡鬧表示,「原音社其實不是一個音樂社團,它是一個社運團體。」
原音社認為,當原運成果盡數被政治體制吸收後,社會仍需存在體制外的抗議路線,才能發揮制衡力量。原音社延續原運的街頭精神,以音樂為媒介,持續關注原住民族權利議題,達卡鬧分享:「我們用音樂記錄一路走來的心境,像〈永遠的原住民〉、〈變色的故鄉〉,就是與族人共同創作的歌曲。」
這個時期,臺灣地下音樂百花齊放,許多小眾、非主流的獨立樂團,漸漸受到市場喜愛。1997年,角頭音樂製作發行《ㄞ國歌曲》專輯,收錄關注不同社會議題的樂團作品,包括五月天、四分衛、董事長、原音社等。「這張專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,代表臺灣地下音樂蓄積的能量,以及音樂如何衝撞社會體制。」達卡鬧說道。
爾後,角頭音樂持續與原音社合作,邀請他們出版正式專輯。為了使專輯元素更加豐富,原音社邀請其他伙伴加入製作團隊,例如鄭捷任、紀曉君、瑪拉歐斯、昊恩等人。這張專輯收錄各族族語、華語、臺語等多種語言,融合傳統古調歌謠和新時代原住民音樂人的創作,並以原住民在部落歌唱時最愛用的Am(A mior)和弦,將專輯命名為《Am到天亮》。
《Am到天亮》具有強烈的原住民主體意識,整張專輯在沉重的控訴中不失樂觀幽默,更展現令人耳目一新的音樂創作能量,是臺灣第一張以原住民族議題為主題的專輯,啟蒙後代原住民音樂人對族語音樂創作的想像力。

原音社昔日表演畫面。
文化並不會消失,
它只是暫時被遺忘
自原運以來,「原住民」一詞似乎標榜著某種身分價值,但參與整個過程甚深的達卡鬧,在近年逐漸有了不同的看法:「可以多接納傳統,但不要過於依賴『原住民』這三個字。」他認為,當今「原住民」已轉變為一種框架,「祖先流傳的文化與知識,教導我們成為社會群體的一份子,即『人』的存在。我們要拋開過去悲情的控訴,放下『原住民』的特殊身分,才能從傳統文化中理解『人』的價值。」
2020年,達卡鬧推出個人第三張專輯《流浪的NaLuWan》,以民謠、藍調、搖滾、雷鬼、頌歌、Rap等曲風,探討NaLuWan與Kacalisiyan(排灣族「住在斜坡上的人」之意)族群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許多人主張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正在消逝,但達卡鬧認為,如同NaLuWan已商業化、刻板化及狹隘化為原住民的音樂符號,但在Kacalisiyan的傳說、音樂、舞蹈和語言中,仍可發現NaLuWan的蹤跡。「文化不會真正的消失,它只是暫時被遺忘,或者流浪到別的時空。說不定等我們到了外太空,會聽到『Naluwan』的歌聲在耳邊響起。」他笑著說道。
當年以音樂對抗主流體制的怒目少年,歷經近40年的歲月歷練,變得柔軟而浪漫。達卡鬧徐徐地說,「音樂反映人性的聲音,我在創作的路上,一直在思考如何藉由音樂促使社會更加和諧,這是我的文化根源教導我最重要的事。」

1988年,跨族群青年團體拉倒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。照片由蔡明德先生提供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