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過去海祭前,男生在3天3夜的訓練期間不能離開海邊,許多海洋知識、漁獵技術都在這時候傳承。現在我想把訓練找回來,拉攏更多青年參與海洋的事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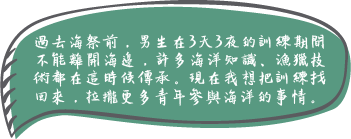

1990年代,噶瑪蘭族的正名運動方興未艾,但同一時期在部落出生的孩子受主流社會影響下,仍以中文為溝通語言,族語成了聽得懂卻無法順暢說出口,既熟悉又陌生的語言。
1989年生、來自花蓮立德部落的lulay inam(林嗣龍),除了面臨語言的困境,也產生身份認同的困惑。百年多來,噶瑪蘭族隱匿於阿美族文化之中,在2002年噶瑪蘭族正名成功後,從小參加阿美族祭儀的lulay,同時「成為」噶瑪蘭族。對於「自己是誰」的疑惑,還有始終無法以母語和家中長輩聊天的缺憾,讓他在29歲那年,決定放下手邊的工作,以全職身份和時間投入噶瑪蘭語復振計畫,以師徒制的方式,回到部落和老人家學習族語。

你知道漲潮和退潮的族語怎麼講嗎?
lulay在兩年多前回到部落,從日常使用的族語開始學起,包括孩提時代累積的一些單詞基礎,到簡單的生活問答如「你吃飽了嗎」、「你今天吃了什麼」,乃至和老人家做歷史和祭儀相關訪談的文化學習。直到今年4月海祭,老人家問了一句:「你知道漲潮和退潮的族語怎麼講嗎?」才開啟他下海的契機。
當時lulay的族語學習計畫已邁入尾聲的第三年,他回答不出來的當下,赫然發現自己對海洋相關的詞彙一無所知。老人家不僅教他漲退潮的族語,也告訴他漲潮時適合潛水,退潮時則能去岸邊撿一些螺類和貝類。
來自海洋的「文化衝擊」,以及在部落伙伴的鼓勵下,lulay開始嘗試入海。從練習潛水起步,學習像長輩一樣在2至3分鐘內,下潛到15至16米深(相當於5至6層樓高),還有學習找龍蝦的棲息地並放置鐵圈捕捉,並從中習得龍蝦的習性,未來打算進一步學如何使用魚槍。

部落婦女在海邊礁岩上採集。
海龜救族人的傳說
lulay曾聽聞部落長輩分享,如果看到海龜,千萬不可以抓牠。傳說,曾有族人落海被海龜救到一個島上,但那是一個無人島,沒有吃的東西,族人便觀察和效仿海龜所吃的海草和生物,因而活了下來,後來這名族人把這些食用知識帶回部落。因此部落族人認為,如果吃了海龜,家裡會發生不幸。
一直這樣下去,
我們永遠學不會抓魚
「海邊的靈,我們會打擾一下,我們等等會在這片海洋潛水和撿一些螺貝類,希望能保佑我們出入平安。」
每一次入海前的祝禱儀式,都是在建立與海的關係,而海洋也會在過程教導族人生活的方式。「在某一年的7、8月看到很多海膽,我們狂撿一大桶,差不多有1百多顆,回去打開第一顆沒肉,老人家看到就說後面的不用開了,全部倒回海邊,因為現在不是產季。」回憶起某次和同伴撿拾的經驗,lulay察覺到海似乎在告訴他們:「海有自己的規律,不是想拿就可以拿」。
除了老人家口中的漁獲量逐年減少,對於正要把自己浸泡回海洋的lulay而言,最有感的莫過於國家在部落和海之間立下的無形界線。從立德部落到石梯坪,是花蓮縣政府規範的龍蝦保育區,公告上寫著「如有必要時,由本府另行公告開放採捕時間」。然而公告時間的不確定性,使得部落長輩無所適從,也為想要學習捕龍蝦的年輕人設下了阻礙。
此外,在海祭前,部落族人有集體出海捕飛魚的傳統,但縣府規定出海必須有船員證,等不到縣府核發公文的族人們也曾與海巡署發生衝突。「最後沒有船員證的年輕人就留在岸上,但一直這樣下去,會抓魚的還是那些長輩,我們年輕人永遠學不會。」lulay感慨地說,「為了因應國家規範,我們也只能多上一些課,趕快取得證明。」

長輩教導lulay製作捕抓龍蝦的漁網。

捕獲的龍蝦。
讓「我們這一代做什麼都不對」
的困境結束
從只會講族語單詞的孩子,到現在已經能擔任同步口譯,lulay在語言學習的過程重新建立起青年與部落的關係。「小時候辦祭儀,我們只會在旁邊玩躲貓貓,所以長大後回來部落,殺豬、殺魚、分肉,我們也不會。」當長輩提到祭儀的分工時,讓lulay不禁心想:「我到底是不是屬於部落的人?有種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好像做什麼事都不對。」這樣的反思,反映出生存在都市化時代的青年處境。
但lulay並未因此放棄,他在5年前和幾位同儕成立青年會,以20到40多歲的青年為主力,以「主動出擊」的方式,在祭儀前主動請教老人家、主動參與祭儀事務如砍竹子、蓋牌樓等。青年會成立後,老人家也知道可以將部落事務分擔給年輕人,他們因此有邊做邊學的機會。「後來我們發現,老人家只是不知道要怎麼教。」lulay笑道。
青年會只是第一步,lulay和伙伴們還計畫恢復海祭前的訓練傳統。過去海祭前,所有男生都必須到海邊接受3天3夜的訓練,許多海洋知識、漁獵技術都在這時候傳承,而訓練時的漁獲則會成為祭儀的經費來源。lulay期許把訓練找回來的同時,也能將年輕族人和海的關係,一起召喚回來。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