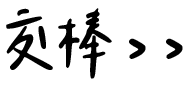過去有手作經驗嗎?今天手作課程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?

我不是很會做手工的人,手很粗,只有用木頭材料包組成飛鼠,很簡單黏一黏的那種。主要是因為我做手工的耐心很少,所以沒那麼擅長,只有畫畫是我可以做很久的事情。
但今天幫風笛竹片削皮,我做得滿好耶,想不到削皮竟然可以!還有幸好做飛鼠皮飾很簡單,不然老師會滿辛苦的。像鞣皮要在皮周圍戳洞時,那個洞我都亂戳,哈哈,可能是平常沒有在做,加上手勁的方向不對,洞的路線就會亂,幸好Voyu最後都還可以收拾。
處理動物皮的感覺如何?

Voyu好厲害,他是我的新偶像,這次過程我一直對比他和自己,因為之前參加類似的文化體驗都是遇到長輩耆老,很少遇到年紀差不多的青年來帶,而且帶的還不是很觀光那種,Voyu是真的很扎實了解這些事物的人。
其實鞣皮技術布農族也有,近年比較有文化意識後,有些青年也開始復振,我因為比較少回山上部落,所以接觸得滿少。當獵人要學的事情太多了,這些「皮毛」事務,是獵人知識體系一部分,我們看不到的知識還有很多,非常敬佩有使命感,而且願意談論、曝光傳統文化的人。
另外就是味道,我小時候回泰雅族的外公外婆家,一直覺得廚房有種「味道」,那個味道是平地人廚房絕對不會有的,我一聞就知道這是原住民廚房。但小朋友不會知道產生味道的原因,直到剛剛我才連結到原來那就是獵物的味道。
小時候常玩的東西有什麼?

電子雞、鬼抓人、芭比娃娃、車子??其實把小朋友放生出去,看到什麼就會玩什麼。我沒有玩過部落「傳統童玩」這類玩具,當時身邊比較沒有會玩這類童玩的人。
轉學到都市以後,我有發現都市同學小時候應該比較沒有在爬樹。因為我小學一年級還住在山上時,家門口都是樹,我滿喜歡爬到高高的地方發呆放空、想事情,或自己玩。有時候爸爸回家,看到我不在,也會想說「Umav大概在樹上吧?」那時候住附近的伯母家有養雞,除了肉雞,還有養五彩花色的矮雞,顏色很多、很漂亮,這種雞的特色就是不愛待在地面,和我一樣愛待在樹上。我記得有一次和平地同學聊說,「我回家的時候,看到我們家的雞都待在樹上,很快樂的樣子。」我講得很理所當然,但同學都覺得我的故事超怪,我後來查資料才知道,原來不是每個人的雞都愛待在樹上。
 短短3天總共有5位老師跟我互動,都是讓我珍惜的吉光片羽。在taso ci Cou楊佩珍老師的田裡學習,他很有耐心地介紹眼前所見的植物和農作知識,我則一直擔心踩到不該踩的東西、砍到不該砍的地方。我在拔地瓜時自嘲只會吃地瓜卻不懂怎麼採,佩珍姐溫柔地說:「很多人都這樣啊!不是只有你。」安慰著不諳農事的我。能夠在山上開闢自然有機無毒農場,同時也是產銷班的幹部,不時還要接待從平地來的觀摩團,我非常佩服這位大姐。
短短3天總共有5位老師跟我互動,都是讓我珍惜的吉光片羽。在taso ci Cou楊佩珍老師的田裡學習,他很有耐心地介紹眼前所見的植物和農作知識,我則一直擔心踩到不該踩的東西、砍到不該砍的地方。我在拔地瓜時自嘲只會吃地瓜卻不懂怎麼採,佩珍姐溫柔地說:「很多人都這樣啊!不是只有你。」安慰著不諳農事的我。能夠在山上開闢自然有機無毒農場,同時也是產銷班的幹部,不時還要接待從平地來的觀摩團,我非常佩服這位大姐。
Sayungu老師是新美的媳婦,從以前就對皮雕有興趣,也喜歡以家鄉元素如地景或動物來創作,有空時也會開課教學。但談到要商品化,他純真地笑說還是喜歡按照自己的心情做事情,作品若是為了販售而做,就必須迎合客人或耗費大量人力。我身為圖文創作者,對他的回應真的非常有感,要多賺點錢,還是保守最初創作的快樂?我忍不住誇姐姐「果然是真正的藝術家」。
Pasuya老師、耆老Mo’o阿公和返鄉青年Voyu,這3位不同世代的鄒族男子也給我很多感觸。首先是Pasuya老師對文化的熟悉和使命感很讓人敬佩,Mo‘o阿公願意花時間和外地青年分享歷史文化,我也非常感激。我常常以自己過去在久美的經驗,或將布農和泰雅的文化默默在心中對照。從他們的分享聽到高一生、林瑞昌的名字,幾經我們詢問,明顯發現對照日本殖民時代,泯滅良心、殘害鄒族生命尊嚴的威權黨國,才是確實對鄒族群體帶來最大殖民傷害的兇手。即使他們在提及相關歷史時,沒有刻意避而不談,也沒有煽動強烈情緒,然而鐵錚錚的歷史擺在眼前,其實我心裡充斥感傷與悸動。
新美(sinvi)這片土地原本不叫新美,是高一生引導族人遷村時取的名字。在口述歷史與考古資料中,這片土地原本是某族群的舊部落,這也是當地鄒語地名Niahosa的由來。Pasuya老師提到這個已經消失的族群叫作「taqupu-aneu」,我從資料發現,這裡據說被視為布農族已消逝的「蘭社」故地,身為布農族人,我能拜訪此地真的很有緣分。
Voyu傳承前輩的培育和期許,扛起文化工作,他是鄒語創作樂團「那麼古謠」的成員,可以流利跟長輩講族語(即使他一直謙卑地說自己講得不夠好)所展現的自信與扎實,讓年齡相仿的人望塵莫及。當我問起他為何在身分證上使用鄒語名字,他不認為其他人一定要這樣,但對他而言,「因為這就是我的名字,我也覺得很理所當然。」那種理所當然的自信、謙遜與凡事不忘尊敬山林先祖的態度,是對我這幾天最重要的提醒。
2022.11.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