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阿魯哇語為臺灣瀕危語言之一的原住民族語,因族群人口數稀少,語言文化幾近失傳,所幸在高齡72歲的游仁貴10多年來不懈地帶領與傳承下,拉阿魯哇語得以跨越世代鴻溝,慢慢看到復甦曙光、往前邁進。
高雄最北端的行政區桃源區位在深山林裡,從市區需行駛1個半小時的蜿蜒山路才得以抵達,而這裡也是拉阿魯哇族主要的居住地。拉阿魯哇族是全臺16個原住民族中,最後一批政府承認的族群,目前僅存不到500位族人,拉阿魯哇語更被列為臺灣的瀕危語言。
20多年前,部落族人開始意識到文化的斷裂,於是挺身而出有系統的整理族語、投入師徒傳承計畫,教導年輕人說族語,如今已陸續培養出數位年輕族人種子教師。而扛起這份傳承瀕危語言重責的人,就是曾獲教育部頒發本土語言貢獻獎、堪稱「現代拉阿魯哇族語之父」的游仁貴amalanamahlʉ salapuana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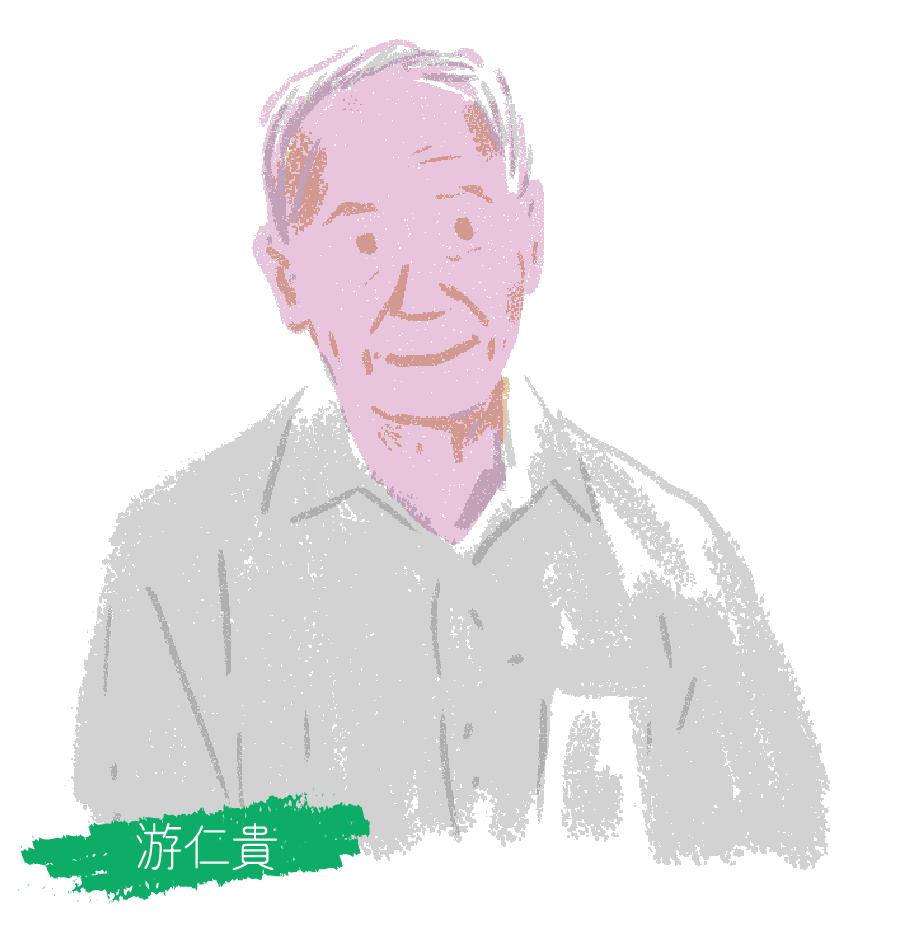
年近半百苦讀羅馬拼音
編輯族語辭典
今年72歲的游仁貴,身上雖流著客家血液,一生卻和部落緊緊相連。他在3個月大時,就由拉阿魯哇族的養父收養,打從有意識開始,游仁貴即認為自己歸屬於部落,「我從小就在這裡生活,部落也養我成人。」
游仁貴自幼就跟著長輩和部落耆老學習族語、哼唱古調,後來受到政府國語政策和外來宗教影響,部落裡的文化、語言、祭儀漸漸消失,就連拉阿魯哇族每年最重要的「貝神祭」,也已有幾十年不曾舉辦。
直到1993年,國家戲劇院辦理原住民族群樂舞展演,拉阿魯哇族的貝神祭受邀演出,成為游仁貴投入文化復振的轉捩點。原來,游仁貴心裡一直有個遺憾,因養父44歲過世時,游仁貴才5歲,小時記憶模糊,認不得養父容貌;當他成年後想找養父的墳墓,卻遍尋不著,「我很難過,一直都找不到養父,以後該怎麼報答?」
因此,當他獲悉國家戲劇院演出消息時,便想藉此找回部落祭儀,報答養父恩情。當時部落還有12位耆老,游仁貴全心全意向他們學習,也鼓勵族人參與,慢慢拼湊出貝神祭的傳統樣貌。事隔50年,貝神祭終於再現國家舞台。
表演結束後,游仁貴原以為終於迎來文化復振的契機,沒想到等了兩年,部落還是無人起身帶頭。游仁貴像是在跟時間賽跑,隨著耆老漸漸凋零,語言流失更快速,心急之下,游仁貴乾脆自己拜訪部落耆老們,討論如何傳承族語。
但光靠口傳還是不夠,原住民族沒有文字,若無法以系統性的方式整理,文化也終將消逝。正當游仁貴苦惱之際,有位德國教授蔡恪恕正好到部落做田野調查,「當時我想機會終於來了!如果我們學會羅馬字,就可以拼音寫字,把口語轉換成文字。」
國小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的游仁貴,以近50歲的高齡之姿,認真研讀羅馬拼音,整整花了1年時間才學會。他用曾經務農的粗糙手指,不停地在鍵盤上敲打,將耆老說過的話全都記錄在電腦裡,也陸續完成圖解式族語辭典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拉阿魯哇辭典,為目前部落學習族語的最佳參考資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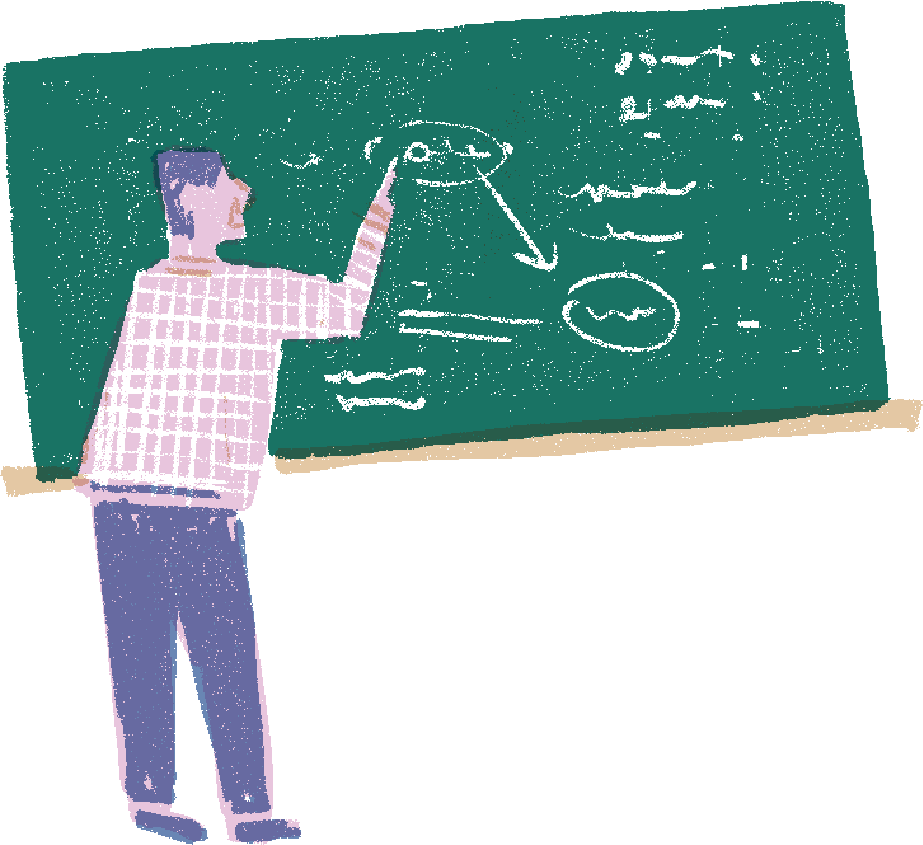

扛起傳承重任
教導中新世代說讀族語
現在部落裡跟游仁貴同輩的耆老只剩下4位,族語凋零得快,游仁貴幾乎是一肩扛起傳承重任。大約從2007年起,政府開始推行原住民「語言巢」計畫,仿照紐西蘭學習毛利語的制度,讓幼童在學前教育就能沉浸在語言環境中,趁早學習母語。當時部落申請此計畫,由游仁貴擔任老師,訓練4位種子老師,每天輪流到族人家裡,推動家庭式的族語教學。後來原住民族委員會又推行「師徒傳承制度」,讓年輕族人1週5天、1天8小時專職學習族語。目前游仁貴教導2位學生,都是20、30歲的年輕人,雖然年輕人學習語言很快上手,但游仁貴坦言,要能流利對話需要更長的時間。
十多年過去,游仁貴至今已培養了7、8位種子教師,學生只要考上原住民語言能力認證高級,就能分發到學校成為族語老師。今年42歲、目前擔任興中國小專職族語老師的vanau savanguana,既是游仁貴的女兒,也是由游仁貴一手提拔。
兩代之間的族語教學,有傳承,當然也有摩擦,「他真的非常固執!有時要花很大心力跟他溝通。」vanau savanguana直言,像是很多中文字詞和族語不相同,游仁貴會根據古老文獻推敲族語意思,但語意可能已與現代用法分岐,此時女兒便需要向他說明、解釋。
雖然偶有意見相左,但vanau savanguana也認同他的做法,「其實他這樣的堅持是對的,不讓我們偏離族語的原意。」比如電影院、影印機這些過去部落沒有的東西,自然就沒有相對應的族語,許多人會直接採用單字諧音翻譯,但游仁貴一定會問清楚這項東西的用途,再用語意解釋,「像是電影院就會翻譯成『以一個很大螢幕看東西的地方』,所以我們的單字才會這麼長。」
以身作則
綿延三代的家庭族語教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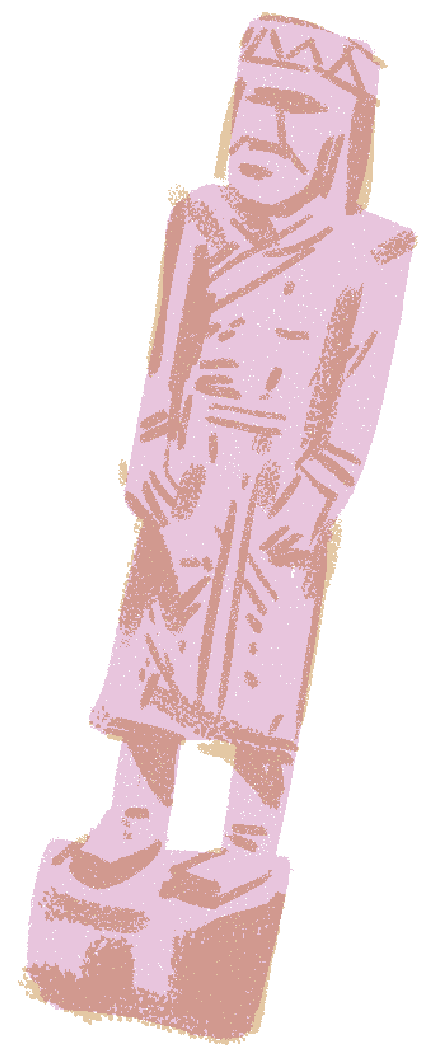
除了紮實的師徒制,游仁貴對家庭裡的族語傳承也非常重視。游仁貴堅持在家只能用族語對話,他的5個孩子全都說著一口流利族語,「我對營造族語的環境很嚴格,不讓小孩看電視、不讓他們聽到其他語言,接電話也一定要講族語。」vanau savanguana笑著說:「雖然爸爸不讓我們看電視,但我們還是會偷偷看,他知道後竟然把電視打破,那時候電視可是很貴的!」
vanau savanguana回想,打從有記憶以來,嘴裡說的就是族語,「小時候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拉阿魯哇人的身分,我只知道我就是這樣講話的,這就是我在溝通的語言。到了學校發現同學都講國語,我們才又去學國語,但一回到家裡,就會自動轉成族語模式。」
當vanau savanguana為人母後,也受爸爸影響,從小在家就和兒女用全族語對話,現在9歲的兒子和7歲的女兒,同樣可以靈活使用族語。他大笑著說:「只要在媽媽範圍100公尺內都要講族語,如果讓我聽到講國語,我就會手刀衝過去彈嘴巴。」
vanau savanguana之所以如此重視族語,也是因為10多年前開始幫爸爸推行文化復振後,驚覺傳承的重要性,「以前都是看爸爸這樣辛苦過來,他做這些事的最終目的,就是不要讓我們的文化消失。我既然當了族語老師,也是文化傳承者,就必須以身作則,把我所知道的傳給我的孩子,」他自豪地說:「我現在也很驕傲現在部落裡的小朋友,只有他們兩個可以這麼流利地講族語。」
每週二是興中國小的「族語日」,學校裡此起彼落的族語聲,像是小小的族語種子,不斷發芽、生根茁壯。木訥的游仁貴揚起害羞的笑容說:「看到越來越多年輕人會講族語,心裡真的覺得很欣慰。」族語復興是條漫長道路,但游仁貴從不喊累,「我要讓養父在天上知道,他沒有養錯這個孩子。」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