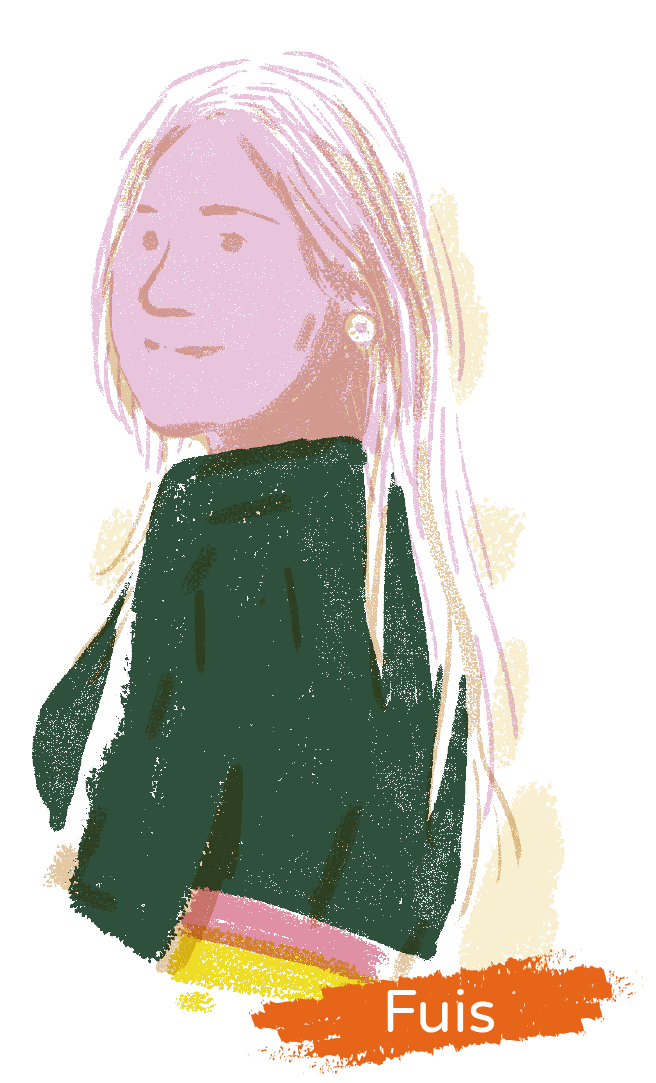 27歲的Fuis Sao Paotawan,是一名跨性別者,男生的身體裡裝了女生的靈魂。過去,他活躍在各式性別運動場合,大學時也擔任過多場性別運動的發起者與主持人,他用自己的生命故事,為大家上了一堂性別教育課。
27歲的Fuis Sao Paotawan,是一名跨性別者,男生的身體裡裝了女生的靈魂。過去,他活躍在各式性別運動場合,大學時也擔任過多場性別運動的發起者與主持人,他用自己的生命故事,為大家上了一堂性別教育課。
Fuis留著長髮、皮膚白皙,有著一雙英氣大眼。如果不說,很難想像Fuis的生理性別是男性。
出生於臺東阿美族部落的Fuis,小時候跟著祖父母生活,直到小學三年級才搬到臺北與爸媽同住。Fuis天生說話平和、舉止陰柔,打從有意識開始,他就覺得自己是女生,加上媽媽的打扮中性,小時候他也常穿媽媽的衣服。
國小時,大人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,只當他還是小孩。國中因為Fuis沒有變聲,家人開始要他講話嘗試低沉陽剛,不要這麼溫柔,這卻讓Fuis疑惑:「家人叫我要像男生講話,但男生講話應該是什麼樣子?我從小聲音就是這樣,我不知道要改變什麼?」
一直到高中交了同性伴侶,父母當時只認為Fuis是同性戀,並未意識到性別認知的不同,「他們就是不談不說,假裝沒有這件事,反正之後分手好好讀書就好了。」Fuis回想往事,輕輕地說道。
靈魂身體錯置
從小穿梭兩個身分
像是靈魂裝錯了身體,在青春期時就連Fuis也對自己感到困惑。當時臺灣對多元性別教育仍不完善,他只能從網路查找資料,慢慢理解自己的性別認同,Fuis到大學才明白,「『性傾向』跟『性別認同』是不一樣的,我是以一個女生的身分去喜歡另一個男生,而不是男同志。」
從大一確定自己是女生後,Fuis開始化妝、穿女裝,也服用女性荷爾蒙藥物,讓身形變得更像女性。在南部就讀大學,平日和父母分隔兩地,但每當回臺北時,Fuis就得換掉女裝,「時間一久,覺得自己快憋死了!為什麼我要一直在兩個身分裡不斷穿梭跟掙扎,這對我來說太痛苦了,我不想要這樣子。」
於是,大二時他鼓起勇氣向爸媽坦承自己的性別認知,對一個保守的原住民基督教家庭來說,父母完全無法接受,也從此與Fuis斷了聯繫。「現在想想會覺得有點後悔,如果當初沒有坦白,或許還能回家看看家人;有時在工作上遇到比較照顧自己的長輩,就會突然想起媽媽,好想要有家的感覺。」雖然Fuis對家庭狀況已能侃侃而談,但家人的不諒解仍然是個遺憾。
投入性別運動
為平權發聲
讓Fuis投入性別議題的起點,其實是來自參與其他運動的經驗。他從小即正義感十足,大學是原住民文化交流社的一員,從大一就為原住民土地正義發聲,也在運動場合中發現關於性別的不平等現象。
「每一次的運動幾乎都是由男性主導,女性永遠負責一些不重要的後勤支援工作,明明是大家一起想出來的東西,為什麼發言的都是男生,我覺得很不公平。」Fuis因此開始投入性別運動,在學校裡舉辦「男裙週」,也和學校的性別平等委員會一起舉辦演講,更主導多場性別活動。
雖然Fuis身分特別,但他成績優異,從小就是學霸,常常上台領獎,身邊總圍繞著一大群朋友;加上他倔強的性格,如果有人用歧視性言語攻擊,他一定會反擊,「我在大學時還被叫做『護理系戰神』呢!」Fuis大笑著說。
反而是畢業擔任護理師後,工作上得面對形形色色的病患和家屬,遭受的攻擊一下子變多了,甚至還曾有人口出惡言:「像你這種人怎麼可以當護理師!」但個性剛強的Fuis,總是會正面回擊,「我有理我站得住,他先汙辱人就是他不對,我會找到保護自己、捍衛我身分的方式。」
即使Fuis的心理素質正面強大,但他坦承,「聽到這些話時還是會難過,不是自己想變成這樣,說真的,要這樣出去,也要鼓起很大的勇氣。」一語道出許多跨性別者的無奈與心酸。
畢業之後,Fuis選擇隱身幕後,不再活躍於檯面上。他直白地說,要持續站在第一線,必須有很大的勇氣,「我站出來所背負的身分除了原住民還有跨性別,要面對的議論非常多,而且遭受指點的不只有我一個人,還有我的父母和朋友。」

三個原因
性別議題難走入部落
投入性別議題多年,Fuis坦言原住民社會接受多元性別的程度仍有段落差,「在部落裡,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人存在,只是不會明著說、假裝沒有。」
他認為原因有三,一是部落教育程度普遍不高,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也就更多,結婚生子、延續家族及部落存續才是重要之務;二是許多族人信仰基督教,對性別的看法較為單一;三是在原住民議題之中,土地正義和文化傳承更加迫切,性別議題排不上優先順位。這些原因都讓推動性別議題更顯困難。
但Fuis指出,既然我們有了性別教育的概念,代表這些觀念是需要「被教育」的,「如果從小做起,當他還是一張白紙時,給這張白紙畫什麼東西,就會出現什麼;但老人家已經是一本故事書,你要怎麼從故事書裡再增加內容,就很艱難。」
這幾年Fuis雖隱居幕後,但仍持續為許多性別活動出力支援,像是參與臺東在地性別平權倡議團體「同寮」舉辦的部落電影院,或是Colorful wi原住民多元性別聯合陣線舉辦的「adju音樂節」,透過電影、音樂等軟性的方式,吸引族人參與,藉機溝通理念。Fuis表示,「透過這些活動讓族人看到,我們其實沒有跟大家不一樣,大家也都生活在部落裡,希望你們可以正視我們的存在,先藉由被看見跟被認可,再去討論怎麼去共同生活。」

性別議題雖然緩慢
但仍在前進
Fuis透露,雖然有時在現場還是會耳聞有人稱他們為「邪教」,但還是有很多人對他們感到心疼,「其實老人家的想法很單純,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社會上受到排擠,所以才希望我們像一般正常人一樣。」
在長輩的年代裡,光是說出自己是原住民,可能就會受到許多歧視對待,原住民已經是少數族群,原住民跨性別者更是形單影隻,Fuis能夠理解老人家們的擔憂,「我們要說服他們,除了把自己過得很好,沒有別的方法。」
他觀察,原住民推動性別議題活躍的時期,大概是近十年的事,但直到現在,Fuis認為原住民發展性別議題的階段還是處於「石器時代,已知用火」。「當臺灣社會已經在講同志結婚、人權,我們到現在還是在做一樣的事,就是讓大家認識什麼叫做同志。」Fuis淡淡地說道。
但Fuis不曾灰心,「起碼現在的人不用再受到我們過往的待遇,不會說『你就不要當我們家小孩』,或是『不要踏進家門一步,你不配擁有這個家的名字。』」性別議題的進程就像蝸牛,雖然緩慢,但仍在前進。「我們也不能催它,只能期待它有一天長出兩隻腳、兩隻手,開始用爬的,或是慢慢學會奔跑。」Fuis的話語輕柔,卻堅定而充滿希望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