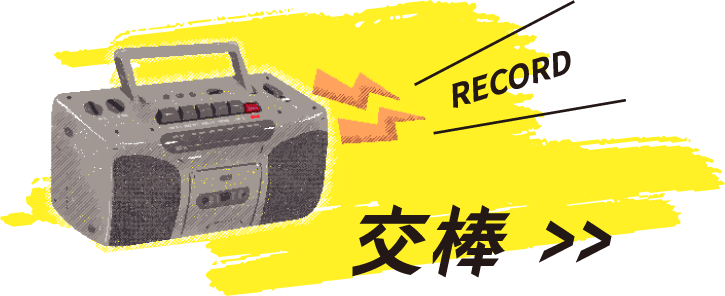恩師許常惠是在2001年1月1日凌晨去世,今年恰巧過了20年。
升大學時,我從花蓮隻身到臺北,在當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菁英薈萃的班級裡,我仍然懵懵懂懂、跌跌撞撞,只暗自決定畢業後要回花蓮教音樂,一時還找不到人生的定位。到了大學三年級參與許常惠老師的課程,他知道我是班上唯一的原住民學生,對我充滿好奇與期待。
老師提到他在1950年的民歌採集運動,和史惟亮組成團隊,踏遍屏東、西部及東部沿岸地區,大規模蒐集臺灣古謠和原住民歌謠。兩年的採集過程,他們發現臺灣許多民族樂壇的盛事,採集歌曲總數量大約有3千首,恆春古謠、哭調等地方歌曲約2百首,其餘2千8百首都是原住民(當時稱高山族)的歌謠,從歌謠內容和歌唱形式可看出豐富的生命力,樂舞更蘊含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涵義。
我低頭聽著老師在講臺上眉飛色舞地談論此事,我彷彿抓到生命的力量,原來原住民的音樂這麼豐富嗎?從小受西方音樂教育,到國中師承郭子究,我都還不明瞭原住民音樂的豐富與獨具的價值。
我抬起頭看著老師,心中開始納悶為什麼我最不願接觸的原住民音樂,老師卻以臺灣瑰寶肯定它的價值?我腦中憶起兒時豐年祭樂舞的現場,不免有種想法──除了舞動與喧鬧的豐年祭,我真的認識阿美族的音樂嗎?就這樣我彷彿找到了未來的方向。
鼓勵我勇敢踏出舒適圈
透過朋友介紹,我來到當時在臺北市中山路中央大樓的史惟亮音樂圖書館,館內雖只有初步的整理,但當我從資料堆裡找到民歌採集運動的音樂帶,耳機傳來既遙遠又古樸的歌聲,我試著跨越自己畫下的界限,嘗試踏出第一步。
畢業後若能在花蓮教學生鋼琴,我就已非常滿足,從沒想過自己會進修碩士。回花蓮多年後,我鼓起勇氣拜訪許常惠老師,表達我想報考師大音樂研究所的意願。起初我先在老師家上課,也展現出對原住民音樂研究的興趣,老師挑出一段原住民歌謠讓我回家聽音採譜,歌謠內容全是自由拍的吟誦及我聽不懂的母語,這對距離部落生活遙遠的我而言,可是非常吃力。儘管只有3段歌謠,我卻將近一週才完成,當我把作業交給老師時,他的臉上浮現訝異的神情,此後我便在老師的鼓勵聲中,走上意外的旅程。
我跟著老師踏入學術的殿堂,也開始把兒時對樂舞的模糊記憶轉變成具體的論述,日復一日地記錄、分類整理、採集樂譜,這也成為我30年田野工作的起點。

愛學生心切而得到一頭牛!
除了巴奈母路,曾參與民歌採集運動的林信來與李泰祥,也都是許常惠的學生,許常惠曾和巴奈母路分享帶原住民學生的趣事。例如過往在國立藝術專科學校(現稱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)任教的許常惠,因看到李泰祥病懨懨的模樣,一問之下才知道李泰祥沒有錢吃飯,許常惠把李泰祥帶到家附近的麵店,和麵店老闆說李泰祥吃麵的費用都算在自己的帳上,月底再一併結清。某天麵店老闆向許常惠結總帳,卻要收2、3千元,而當時一碗麵只要3元,許常惠驚訝地問李泰祥,「為什麼會花這麼多錢吃麵?」李泰祥說他在臺北的家人沒有錢吃飯時,也會到麵店吃麵,並把費用記在許常惠帳上。許常惠疑惑,這樣怎麼有辦法還這筆錢?李泰祥只說他會再想辦法。過幾天,學校操場草皮上突然多了一頭牛,李泰祥和許常惠說:「老師,這頭牛是用來抵帳的。」許常惠差點昏倒之餘,想到李泰祥的家人辛苦地從臺東趕牛上臺北,這份誠摯讓他大受感動。

為人師表的典範
我後來問過老師,為什麼這麼關注原住民音樂人才的培養?老師回答,早期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到臺灣研究原住民音樂,他和許常惠說:「臺灣音樂研究應該要由臺灣的學者來做。」這句話鼓舞了許常惠,因此才出現1960年代的民歌採集運動;過了30年,老師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:「臺灣原住民音樂應該由原住民音樂學者投入才對。」
在開放兩岸探親初期,老師即前往中國大陸采風與學術交流,並時時叮嚀我要留心滯留在中國的原住民傳統歌舞保存狀況及變化。那時,兩岸學者往來頻繁,1993年老師甚至帶我參加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討會,現場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為14個不同族群的統稱,而非僅高山族一族的概念。藉由老師屢屢穿梭兩岸,更在國內引起民族音樂學界一陣風騷。
距離許常惠離世已20年過去,臺灣樂壇已經很少人會提到老師的名字,但是在跟隨他的時光中,他對我的鼓勵、提攜與教導,猶如海上遠處傳來的鐘聲跟雲彩,既悠遠且繚繞。許常惠在民族音樂學界出言的分量一言九鼎,為人謙沖有禮,穿著打扮風采翩翩,而宴席上又能放懷高飲,讓同席者皆盡歡。老師見過各種大大小小的場面,上至高官下至販夫走卒,閱人無數,但老師對學生很是客氣,不忍見學生背著經濟重擔,往往會帶學生到他常去的飯店小館用餐,顯見老師的平易近人。

1977年夏天,許常惠探訪屏東縣三地鄉。
沒有他,就沒有今日的我們
我自1984年開始接觸阿美族的祭儀樂舞,每一年的田野採集累積許多疑問,因為祭儀音樂為既豐富又晦澀的文化知識體系,老師總是鼓勵我多花費心思整理田野的影音資料,哪怕只是以一天的巫師祭樂舞為基礎的分析與整理。因著老師的期盼,我在1992年進入師大音樂研究所進修,於論文中整理出23首巫師祭祭歌、歌詞、禱詞,以及一天的儀式整理,雖然資料與紀錄仍然殘缺不全,對我而言卻是收穫滿滿。
1995年畢業後,為了專心從事原住民音樂研究,我離開教書的行列,並在老師的支持與父母贊助下,於1997年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,開啟我另一段孤獨和陌生的旅程。
老師頻繁來往兩岸,且因當時國內未有音樂學博士學位的課程,他曾詢問我要不要去中國就讀博士班,但我的外文能力不佳,也從未想過出國念書,特別是兩岸氣氛仍不明朗。但老師的大力協助,讓我毅然決然到中國開拓眼界,老師更抱著託孤的心情,將我交付給未來博士班導師。在結束博士課程後,我也完成「靈路上的音樂──阿美族歲時祭儀音樂研究」,論文中形塑音樂特質的8種3個音與排列組合,以及襯出靈與靈在天地人之間互動關係的「襯詞」(ha hai、ha he),都是我原創的論述。如果沒有許常惠老師,就沒有這些原住民主體性音樂文化知識體系建構的空間,更不可能有時至今日仍在部落從事田野工作的我。

1978年8月6日,許常惠到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,留下與布農族人合影一圖。
 巴奈母路 Panay Mulu
巴奈母路 Panay Mulu
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,研究領域為民族音樂學、原住民文化展演與樂舞、阿美族祭儀文化,以及音樂人類學。曾出版《繫靈:阿美族里漏社四種儀式之關係》、《靈語:阿美族里漏「Mirecuk」(巫師祭)的luku(說;唱) 》等書。